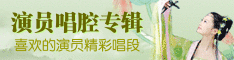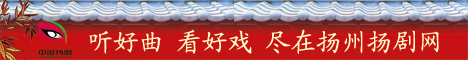中秋之夜,玉匠刘庆昌远途销货归来病倒城外关帝庙中,哀求卖粮球老人赵庆送信给妻子韩素娘救援。途中赵庆被刘的妹婿吴诚道骗开。吴为赌债所逼,抢走妻兄银包,并将其谋害致死。刘翠娥见兄暴死,痛不欲生,听信丈夫吴诚道诬陷,误认嫂子与人通奸杀夫,悲愤交加,进衙告嫂。吴诚道呈状司房。贿赂县衙令史肖仁,将韩素娘定成死罪。韩素娘不甘蒙冤而死,狱中血书冤帕。刘翠娥在姑母陪同下抱侄探监,见到韩素娘抚孤哭夫,肝肠寸断,又听姑母辩解,方知错告了嫂嫂,愧悔之余决定寻找原凶。经查询送信人赵庆,又在家中发现被劫银两包袱,通过盘问斗智,终于真相大白,杀兄真凶乃自己丈夫吴诚道!吴诚道面纱被揭,急于肖仁谋划,星夜将韩素娘送到府衙问斩。刘翠娥不顾身怀有孕,拦路鸣冤,惨遭毒打。在刘庆帮助下,闯府衙告亲夫伸冤屈,替嫂翻案。然而河南府尹彭威凭经验、重呈文,不信申诉,待发觉错判时,清白无辜的韩素娘已经人头落地。刘翠娥悔恨交加,公堂之上触柱而亡,一腔热血为嫂洗冤……
《血 冤》
1984年,在江苏省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调演中,扬州市扬剧团编演的新编大型古装悲剧《血冤》,脱颖而出,引人注目,获编、导、演、音等诸项奖,同时获得江苏戏剧最高奖,第三届戏剧百花奖的优秀剧本奖(刘葆元、汪琴)、优秀导演奖(刘静杰、邱龙泉)、优秀表演奖(李开敏)、优秀演出奖(《血冤》剧组)。
扬剧《血冤》上演数百场,成了扬州市扬剧团打炮戏,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演出,剧场效果强烈,好评如潮,有人说扬剧《血冤》是一出令人荡气回肠的悲剧。有人评价《血冤》是“别开生面写冤狱”。有人说:“撼人心弦、摧人泪下、发人深恩”。有人赞誉:“《血冤》是一朵璀璨的扬剧之花”。
扬剧《血冤》的成功,用导演的话说:“因为它有一个健康的主题——颂扬真善美,鞭挞假恶丑”。这无疑是建设精神文明的需要。还因为它有一条贯穿全剧的主干线——原告为被告翻案,凭着这一中心事件决定剧情的起承转合;决定人物关系的转化与人物命运的转折;决定舞台节奏的起伏波澜。因而有戏可挖,有戏可演,有戏可看。更因为它有一个血肉丰满的主人公——刘翠娥。一个普通的古代女性,善良、纯厚、疾恶如仇,因受蒙蔽而错告了嫂嫂,一旦觉醒,便不惜一切,呼号奔走,为嫂伸冤,最终以鲜血洗刷自己过错。感人之深、震撼我们的心弦,相信,同样能打动观众的心。用扬州师院中文系李关元教授的话说:“血冤”的成功在于它跌宕起伏的戏剧结构,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,发人深思的思想内涵和生动传神的表演艺术。《血》剧展现了郎舅之间、姑嫂之间、夫妻之间的纠葛,虽矛盾重重,但线条清晰、脉络分明,戏剧冲突一环扣一环,戏剧高潮一浪高一浪……,戏剧结尾不落窠臼,善良无辜的韩素娘和疾恶如仇的刘翠娥的死,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,这一别出新意的结尾使主题得到更深广的开掘。在吏治腐败、世风不正、人欲横流的社会里,纵有彭威那样的“清官”也会造成千古奇冤,观众面对这样的剧情或叹息、或怜悯、感悲愤、或陷入深深的沉思……
上海报人评价《血》剧是一出令人荡气回肠的悲剧:吴诚道、刘翠娥的丈夫,这个腰缠药葫芦的郎中,一念之差,铸成大错,一步一个深渊,让人担心,惋惜到切齿痛恨,这是一个自我毁灭的悲剧人物。
刘翠娥嫉恶如仇、性情刚烈,由轻信丈夫吴诚道诬陷、误告嫂嫂通奸杀夫,待真相大白、杀兄凶手乃自己丈夫,她肝胆俱摧、痛不欲生,当她不顾身孕追到河南府衙、闯公堂为嫂鸣冤翻案时,嫂子已命归黄泉,悔恨交加地喊出“我是凶手”,当场触柱而亡,不啻如一块白玉自毁,令人心碎。
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陈超看过《血》剧,在新华日报发表短评“好一个刘翠娥”,赞刘翠娥一身正气,融真善美于一身,正义感很突出。
1984年12月8日,年近八旬的孙浩然教授(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长、上海剧协副主席、原上戏副院长)偕夫人顶着严寒驱车往邗江酒甸观看扬剧《血冤》,很激动,边看边议,他认为该剧是一出十分精彩的好戏,从剧本到表、导演,各方面都下了功夫,有自己的追求和突破,尤其“识真”这场戏,化用了“活捉张三郎”里的一些传统表演手法,推陈出新,用得贴切、神奇。《识真》是《血冤》的重场戏,唱做并重,汪琴扮刘翠娥、刘葆元扮吴诚道,刘翠娥四处奔波未寻到知情人踪影,十分焦急,突然卖糖球老人出现在他家门前,她喜出望外、急切询问,当她从老人话语中悟出凶手与丈夫吴诚道模样相像,如当头一棒,浑身颤抖,用一组大幅度水袖组合和着“满江”过门,把难以自持的紧张、恐惧宣泄而出。当唱到“世间上人常有同模同样,我胡乱猜疑太荒唐”时,她否定了前面的想法,作自我安慰,节奏趋于平和。当发现药坛中的砒霜不见,却盛放着弟弟从湖广带回的银元宝,松驰的神经突然绷紧,一个停顿、一个转身,用身体遮挡着药坛、屏住呼吸,她不敢想、不愿想,又不得不想,心里默念“真的是他?!”嘴上却念念有词“不会的,不会的!”这声音近于哭泣。丈夫回来了,她开门,二人对视,停顿中伴唱起:“举止潇洒模样儿美,是人还是鬼?”缓缓走了个磨盘调度,身子向前靠拢丈夫,审视他,再向后退去,水袖垂地,视觉里出现的是狰狞面目与和颜悦色交替更迭。她听到丈夫亲热的呼唤,看到他为未出世的姣儿带回的长命锁,对丈夫的怀疑荡然无存,他陶醉在儿女之情中,与丈夫相伴相搀,踏着抒情的乐曲同步坐上床塌,水袖温柔地搭在丈夫肩上,身子深情地依偎在他的怀中,无意中手触到葫芦,似电击一般,因她想到卖糖球老伯所说,凶手腰间挂个葫芦,在失控的一声惊叫后,离开了吴诚道,恢复了理智。在盘“夫”一节,她眼神专注,话锋犀利,时而欲擒故纵,时而紧追不舍,时而若谈家常,时而犹审犯人,吴诚道终于露出破绽,当发现赃证——包袱藏在家中时,刘翠娥抓住包袱在手中旋转,以示头晕目眩,紧接“梳妆台”过门加打击乐配合,表演了一组动作幅度较大的身段,揭示她胸中极大的悲伤与愤怒。在“控诉”一节,借鉴“活捉”表演,用“莲花调”演唱,在单板弹跳的节奏中,旦进、生退,最后借用一把椅子作砸椅、架椅、拖椅、转椅、坐椅的动作,把戏推向高潮。看后孙教授说:“好极了,调度、水袖、椅子用得如此好,若到国外演出,中国的戏曲传统一定会使他们惊讶”。临行还说:“这次来扬州仅仅看这一出戏,就很值得。”
《血》剧的成功,还得益于演员的表演功力,汪琴与刘葆元做表生动传神、舞台配合默契,让观众赞不绝口。“夫妻写夫妻演夫妻”成了一段梨园佳话。
李开敏饰演的韩素娘一角也是《血》剧中一抹亮色,她用心塑造了一个无辜、善良、含冤,不日便成刀下鬼的屈死者的艺术形象,尤其在“探监”一场以“情动于衷”、“声情并茂”的唱腔魅力感染着观众,62句一段唱腔,唱得委婉、凄楚,字字血、声声泪,撼人肺腑,催人泪下。她深入角色内心世界,从不多行一步,不多抖一袖,她贯穿全剧的台步是碎步,贯穿的性格是忍辱,贯穿的眼神是忧郁。恰到好处地演绎了一个带着铁炼跳舞的死囚形象。
《血》剧后来改编成同名昆剧,由江苏省昆剧院演出,获文华剧目奖。
本文引自:扬州扬剧网(www.yangju.cn) 原文参考:http://www.yangju.cn/article/yangjuxiping/2009/1031/14234.html